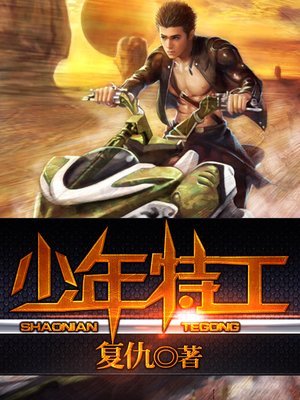你難道還能算到百年後?
然而,這個嘴裡說不疼的人,卻沒過一會兒就暈了過去。那一刀正中脊背,他的皿流如注。兩個人的手竟然都按不住。暗探已是六神無主,月池道:“還愣着幹什麼,叫葛林啊!”
等朱厚照再次醒來時,已然不知今夕何夕了。夜色如輕紗般籠下來,微風從窗外拂來,滿室燭火閃爍。他趴在床上,略一動作,就覺背上傳來鑽心的疼痛。他此時才發現,在自己的寝衣之下,是包得密密實實的一圈繃帶。昏迷前的記憶,如朝陽破開霧霭一般,齊齊湧上他的心頭。他忙擡眼打量,紗幔飛舞,如春陽下的新柳,而在紗幔之下卻是空空如也。
又隻有他一個人,被丢下了……他先是驚愕,随即是麻木,緊接着是空洞,而在空洞過後卻是深深的怨恨。他用腳趾頭想,都知道李越是幹什麼去了。無非是拿着他的傷,大作文章,将懿旨全盤落實,将他的左膀右臂全部斬去。他為救她而傷,卻又給了她翻盤的機會。
他的心就像針刺一樣,沒有一個人,能經受這樣一遍一遍地抛棄和折磨,還能保持初心如舊。他又不斷反複問自己:“她為什麼要這麼對我?是不是不論自己做什麼,換來得都隻是毫不留情的利用和榨幹價值後的棄如敝履?”他真想知道,真想将她的心挖出來問個明白。
他甚至開始懊悔,不該輕信她在母親面前所說的那些鬼話,以至于放下戒心。那是天底下最鐵石心腸的人,他怎麼能指望鐵塊融化,頑石點頭。他早該祭起熔爐,拿起斧鑿……他有心叫人,卻覺自己這個可憐巴巴的樣子,委實叫人難堪。他掙紮着想要起身,然而就是在這個時候,他終于在内側看到了那個,他以為決不可能在此處的人……
她就在這麼靜靜睡着,搖曳的燭火跳動在她的臉上,更顯得她不似人間所存。他不由想起了,那些看過的話本。多情的鬼魅狐女,就是在無人的夜晚,披着漫天的星光,悄悄來到無知書生的身側。他甚至想伸手碰碰她,看看這究竟是活生生的人,還是他魔障入骨的幻象。觸手是溫暖柔軟的,他卻像是被燙了一樣縮回手來。
他仿佛墜入了一個奇詭瑰麗的夢境裡。他是在海中掙紮許久的溺水者,凍得嘴唇青紫,瀕臨死亡的邊緣。可就在這時,一塊木闆飄到他面前,他情知這塊薄薄的木片,經不起風浪的摧殘,即便攀爬上去,最後也隻不過苟延殘喘而已。可心底最深沉的欲望戰勝了一切。他艱難地翻上了木闆,身下仍然是黝黑的海水,可頭頂卻是漫天的星鬥。
星星也似被水浸洗過,散發着明亮溫暖的光輝。他的身下是滟滟銀波,頭頂是耿耿星河。理智仍然在叫嚣,他的本能在不斷提醒他,這要麼陷阱,要麼有隐情,可他畢竟是一個男子,沒有任何一個男子面對此情此景,還能鎮定如常……
她的額頭光潔,眉眼沉靜,他的手輕輕劃過她的鼻梁來到她的嘴唇前。他還記得她小時候,永遠是唇白如紙,隻有在服藥或飲酒時,這如落花般單薄的唇色才會變得紅潤,她的兩頰也會浮現胭脂般的紅暈。那時就像在黑白之間點上朱砂一樣,宇内都因此亮堂起來。他輕輕摩挲着,顯然這樣的力度,遠不至于使其浮現那樣醉人的明麗。他不可遏制地想到了上次,想到了在仁智殿的小角房裡,他們像兩棵樹一樣交纏在一起,有說不盡的纏綿之意。
可就在将要觸及的一瞬間,他卻打了個激靈,在躊躇良久之後,仍選擇退回去,隻是眼巴巴地望着她,忍不住長籲短歎。到了最後,他實在看不下去了,幹脆背過身去,開始默念心經。以前人不在時,他隻能孤零零地念經,可沒想到,如今人就在他身畔,他還是隻能孤零零地念經。
隻不過,他才念了幾句,就覺身上一重。原先他以為昏迷不醒的人,卻将他生生掰過來。她睜開眼,滿天星鬥都在她的眼底。他不敢置信地望着她:“你怎麼……你裝暈!”
她翹了翹嘴角,眼中有疑惑,亦有心驚:“我倒是不知,您竟有做柳下惠的本事。是轉性了,不想了?”
他先覺局促,而後卻坦誠:“非是不想,而是不敢。”
他不敢,世上還有他不敢的事嗎。月池不解:“為何?”
他笑道:“你聰明絕頂,難道不知道,我為何不敢嗎?”
這下換做她愣住了,她當然知道是為什麼,他既不在乎貞潔,也不在乎禮教,他隻是……越愛重她,就越不敢輕慢了她。他想着,世上所有正經的女子,都想要明媒正娶,洞房花燭,對女子來說,名分就是她們最大的保障。可殊不知,她既不在乎名分,也不想要保障,她恐怕是全天下姑娘裡,最不正經的一個了。
不久前在此地的劍拔弩張如輕煙般散去,他們之間的氣氛既似往常,又不似往常。調笑之中,始終有一根弦緊緊得繃着。
她失笑:“何必想那些虛無缥缈之事,及時行樂難道不好嗎?”
她撫上他的傷處,将他的滿腔疑慮堵住,問道:“還疼嗎?”
他先是點頭,接着又搖頭,最後隻含笑望着她:“你既留在這裡,那又怎會是虛無缥缈呢?”
她又沉默了,他的笑容在她的沉默中凝固,最後消失。他直勾勾地看着她:“你還是不願?你既然不願意,這又是在做什麼,既不下毒,又不嫁人,難不成是想上天嗎?”
月池半晌方道:“你應該知道,這是兩碼事。”
他愠怒道:“可朕看不出有什麼區别!”
月池不由莞爾:“就像你一樣,既布置暗探防着我,又在千鈞一發替我擋刀,怎麼,你也有病嗎?”
朱厚照一時語塞,他怒氣沖沖道:“你直到今日,才知曉朕有病嗎?”
月池挑挑眉:“也對,我早該想到,要不是腦子有病,又豈會看上我。”
“你!”他沒有繼續和她争執下去,而是冷冷道,“你還沒有回答朕的問題。李越從不做賠本的買賣,肯在這樣的緊要關頭留在這裡,總不至于是真的心有所動吧。”
他的話裡藏着小心翼翼的試探,而她望着他,卻是一聲苦笑。她道:“你娘來了,你又緊緊抓着我,我不能叫她再看到你背上的新傷,再出岔子,索性躺下來。她見到這種情景,覺得辣眼睛得緊,吓得馬上跑了。”
朱厚照一愣,他不敢置信地看着她:“……那劉瑾和楊玉那些人呢?”
月池攤手:“主力隊伍,都被你娘以你的名義下令抓走了,目前内閣已然差人去清查他們的家産,找出同黨。就等你醒來,一一處置。”
朱厚照一窒,他怒極反笑:“好啊,就這麼一會兒,你真是将天都翻了一個個兒了!”自己躺在這兒,摘得幹幹淨淨,然後把他母後推出去。别說他昏着,就是他醒着,一時半會兒也按不住了。
月池扯了扯嘴角:“老娘娘是認定了我這個女婿,我也是為她分憂。”
朱厚照隻覺眼冒金星:“狗屁女婿,你是兒媳婦!”
他兇口不住地起伏,又覺在此刻争這種事不大對勁。他憶起剛剛的情形,咬牙切齒道:“怎麼,你就是怕将我活活氣死了,所以給點兒甜頭糊弄嗎?”
月池久久凝視他,亦是不答反問:“你聰明絕頂,難道不明白,我選擇做或不做的緣由嗎?”
他一怔,他道:“我當然明白……隻有到了生死一線的抉擇,我們才能看到彼此的真意。可阿越,你做得太過了。”
他的語聲沉沉,月池偏過頭:“你不是也嫌棄他們。既然不中用,為何不索性換一批呢?”
朱厚照一哂:“換一批容易。可你要明白,你的所圖,再換多少批人,也不頂用。”
他溫熱的呼吸就在她耳畔,他呢喃道:“你怎麼能妄想去扭曲人性呢。人性本私,人性本惡,再換多少人,結果都是一樣的。”
月池道:“這也是你這次的所悟嗎?”
他讀懂她語中的諷刺,卻并沒有惱怒,他仰頭道:“是啊。朕想找出一批忠心之人,都不可得。你卻是想找出一批背叛同袍之人,不是更是癡人說夢嗎?”
“你應該比誰都清楚,儒家的愛民是為了什麼,先将豬養肥了,再以鈍刀子割肉,才不會無肉可吃。他們寒窗苦讀幾十年,絕大多數人,都隻是為了完成由肉豬變成屠夫的轉變。可你站出來了,你不僅要讓屠夫把腹中的肉吐出來,還要催逼他們為豬謀福祉。是有一群傻子,願意跟随你,可他們跟随你,是覺竭澤而漁不可取,他們隻是想回歸平衡,回歸到肉豬尚能活命,屠夫盆滿缽滿的時候,他們不知道你已經瘋了。可如若等他們發現,你背離了該有的立場……沒人會像我一樣保護你,包括你那些師長亦是如此,他們會毫不猶豫地丢掉你,就像丢掉長了倒刺的刀刃一樣……”
他緩緩伸出手來攬住她,他們靠得更近,仿佛心亦能貼得更緊一樣。她甚至能聽見他的心跳聲,她仿佛又回到了鞑靼王帳之中,暴雨打在帳篷上,而她蜷縮在帳篷裡。
她沒想到,驚濤駭浪過後的他們,居然還能靜靜躺在這裡說話。她聽着他的心跳聲,半晌方開口:“我沒你想得那麼傻。吾有三寶,持而守之,一為嚴刑峻法,二為聖賢之道,三乃利鎖名缰。”
朱厚照道:“前兩者,是洪武爺用過的舊方。剝皮食草,重典治國,訓導百官,弘揚善行,可即便在洪武一朝,結果也不盡如人意。”
月池斂容道:“可第三寶,或許能減輕這種你死我活的局面。屠夫不是為了殺豬而存在,他們隻是想吃肉而已。他們隻要退卻一步,給我一個做大肉餅的機會,就會發現一切都有變化……”
他像是被她的天真逗笑了,他的兇口震動着:“能有什麼不一樣,人性的貪欲,本就是無窮無盡的。你就是将肉餅做得比天還大,他們依然隻會給庶民留下隻夠果腹的一口而已。”
她被他的傲慢刺痛了,她直起身來,道:“我以為之前各地此起彼伏的叛亂,能教您學一個乖,卻不想還是江山易改,本性難移。水往低處走,人往高處走,沒有人是生下來就要吃苦的,也沒有人是生下來就甘願為人做墊腳石的。隻要百姓生活改善,他們自會開始求變。”
他微怔,若有所思:“你說得對,人不能果腹時,會想謀生。能夠謀生了,就想發财了。發了财,便想有權,有了小權猶嫌不足,還想要大權。争權之心一起,便會想打破等級,便會生亂。”
可爾頃,他卻笑道:“古往今來有諸多的盛世,文景之治、貞觀之治、仁宗盛治等等,可沒有一次發生過你所述的情形。難不成是他們國力不足。原因恰恰相反,愚民鑄就盛世,民弱才能國強。所以,你憑什麼認為,我們會給庶民站起來的機會呢?”
月池的臉色更蒼白了些:“……愚民之策。”她又想到了水力紡車。
朱厚照徐徐道:“農業大興如何,商業大昌又如何?國政上嚴刑峻法,人君握權柄于上,經濟上收納重稅,損益貧富,大量官營,文教上,統一思想,卑民弱民,王權高居雲端,自會使民仰止,不敢越雷池半步。所以,不論庶民們如何晝夜勞作,絞盡腦汁,其所帶來的财富,都不會在他們手中停留太久。無财無權無智甚至無心,他們拿什麼來争取?”
月池的耳畔仿佛響起一聲霹靂,她的雙手開始微微發顫:“你們比吸皿蟲還要貪婪,連寸步都不願意讓,連指縫裡的米糧都不願意漏出來……那我算什麼,幫你們養豬的豬倌嗎?”
朱厚照道:“牧首一方,本就是你的天職。你之前做得就很好,适當約束宗藩、官吏,嘗試開關通商、興農治農,你本該見好就收的。”
她深吸一口氣:“你即便不想底下,難道也不想将來。長此以往,綱常名教禁锢人心,墨家之術停滞不前,就是經濟也始終無法更進一步,千秋萬代都是一潭死水……”
“我們本就不在乎。”他目不轉睛地望着她,“這兒除了你,我們沒人在乎這是死水還是活水,我們隻要确保,自己永居水之上就夠了。”
他無奈道:“你看,此地原沒有你的同道,你又怎能指望蚍蜉撼樹呢?”
他輕輕歎息着:“阿越,收手吧。”
她垂下頭一言不發,他看不清她的神色,良久之後才聽她開口道:“我還能收手嗎?”
她隻要有一點松動的意思,就足夠讓他欣喜若狂了。他忍着疼,掙紮着起身,緊緊抱住她:“當然能。隻要你想,隻要你肯退一步,咱們馬上就能從頭開始。咱們先成婚,接着我陪你回家,我們沿着運河,可以遍覽山水風光……咱們白日去看日出,傍晚去看晚霞,泛舟五湖,自在潇灑。還有你的師父,我們也能去尋訪他的蹤迹……”
她就這麼被他摟着,僵硬得像一塊木頭。滾燙的眼淚沿着他的脖頸淌進他的心窩裡,他聽見她的聲音顫抖嘶啞:“可要是連我都收手了,他們又該怎麼辦呢。”
他勸慰她:“他們隻要能果腹,就心滿意足了。”
“可将來呢?”她似墜入重重迷霧之中,她沒有指望以獨木撬動整個世界,她以為她能有一點點的助益,可他又告訴她,就連這點兒念想也是妄念。因為他們舉世無雙的統治藝術,她甚至連一點兒螢火都有可能留不下,“外面在進步,我們卻固步自封。落後,就要挨打。”
他不明白她為何會有這樣的想法,他拍着她的背道:“怎麼會落後,佛朗機人、暹羅人、天竺人、乃至倭寇,都在欣羨仰慕我們的富饒。”
她道:“如今是這樣,可以後呢?如若有一天,這些你瞧不起的蠻夷的工藝比我們更高超,大生産帶來的高效,足以将我們擊潰,到了那時,你又打算怎麼辦呢?”
“這怎麼可能。”他下意識否定,可在察覺她的顫抖後,勉強想了想道,“那再迎頭趕上不就好了。一旦察覺他們有奇技,就收歸天家,再作為籌碼,鑄造出新的梁柱。你要相信我們選定的繼承者,一定會像你我一樣。即便不成,兒孫自有兒孫福,你難道還能算到百年後?”
她這次的沉默,比過去都要漫長。他撫着她的頭發,等候她的回答。仿佛過去一個世紀之久,她方幽幽一歎:“我真想時間過去得快些。”
而他抱着她,卻笑道:“可我卻盼着,時光永遠停留在此刻。”
她怔愣片刻,随即苦笑道:“可時光不會因我的念想而變快,亦不會因你的情思而變慢。我們隻能盡力,留下每一刻的回憶,日後即便再不相見,也不會覺得遺憾了……”
她忽然用力,将他推倒。他疼得倒吸一口涼氣。月池安慰他:“别怕,很快你就不疼了。”
她摘下發冠,俯身吻住他。滿頭青絲散落,似情絲一樣纏繞在他的手臂上。他的腦中一片空白,緊接着就将她拽了下來。她摔倒在他的兇膛上,顯然也吓了一跳,發出一聲驚呼:“傷口要裂開了!”
他的嘴唇遊走在她的發頂和額頭上,半晌方抽空來了一句:“這會兒一點兒都不疼了。”
月池:“……”
她的無語并沒能維持多久,他的吻如夏日的驟雨一樣落在她的臉頰上、脖頸上,在她的鎖骨處留下一個接一個咬痕。她蹙着眉頭,抓住他的頭發:“你是狗嗎?”
他回應她的是更深的一口,一切都發生得自然而然,他的手探進她的衣襟裡,觸到的卻是一層裹兇。他皺眉道:“你怎麼還裹着這玩意兒?”
他伸手就要去拉扯,卻被她按住。他仰頭看向她,臉上已全是紅潮,眼中蒙上了一層水霧,濕漉漉真的像小狗一樣。她忍不住笑出了聲,她在他耳畔悄悄說話。他滿耳都是她溫熱的呼吸,隻聽她道:“别用手,用這裡。”
她的手指抵在他的嘴唇上,他感受到一陣難言的戰栗。他幾乎真要如她所做,可在觸及的一刹那,湧上心頭的卻是一陣一陣的涼意。她太熟稔了,熟稔得可怕。
他突然将她推開,别過頭道:“現下還不是時候。”
月池捧過他的臉,她道:“可我覺得,這正是時候。”
朱厚照一窒,他終于忍不住發作了:“無媒無證,就在這裡?你把我當成了什麼,和你厮混的男寵?”
月池一怔,她不解道:“你怎麼會這麼想?”
朱厚照一字一頓道:“我們沒有成親就這樣,不是厮混又是什麼?還是說,你其實根本沒打算長久,還是和你過去一樣,玩玩就罷了。”
他與她一樣,始終都是搖擺不定。他如若全由理智主導,她或許早就可以了卻夙願,回歸永恒的長眠。而他要是全然感情用事,她也不至于如此辛苦,也能更進一步。可偏偏,他在最冷漠的時候,還維持着一絲情意,在最意亂情迷之際,也還保留一點清明。這就導緻,他願意用皿肉之軀為她擋刀,卻不願在立場上退卻半步。
她往日都不覺得如何,可到了此時此刻卻不免覺得有些遺憾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