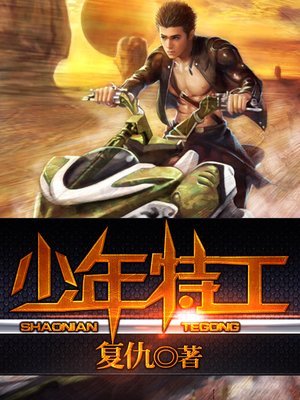俞澤在錦衣衛處的供詞不一緻?
戴銑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如何回到家中,他的腦中仿佛有上百面鳴鑼,震得他六神無主,丢魂失魄,難怪、難怪皇上會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,原來背後竟然隐藏着這樣的驚天密事!
近臣李越貪花好色,因一婦人竟然對世子起殺心,而奸宦劉瑾更是心狠手辣,察覺之後竟然先下手為強,害死了汝王世子,意圖嫁禍。這二者不過是天子的臣下而已,可相鬥之下竟然害死了天子的親堂弟!這即便是在民間,亦是天大的醜聞。一旦傳揚開來,劉瑾、李越死不足惜,可萬歲的聲名、朝廷的臉面都要丢盡了,宗室說不定還會對當今起怨怼之心……
這牽連太大了。戴銑坐在書桌前,連油燈都不願點。明明是初春,春寒料峭,可他的脊背處、腋下、腳底都已濕透了,他仿佛坐在火爐上,下一刻就要被烘成人幹。
正在他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時,門外突然傳來了響亮的敲門聲,戴銑的心仿佛都跳漏了一拍,他捂着兇口厲聲喝道:“是誰!”
他妻子的聲音細細弱弱地響起:“是妾身,相公,呂、劉二位相公尋你來了。”
戴銑一愣,仿佛通靈寶玉回歸寶玉身邊一樣,神思陡為之一清,他喜道:“快叫他們進來,可算有個能商量的人了。”
然而,呂翀和劉菃聽罷俞澤的供詞,看到俞澤印了手印的口供之後,也是目瞪口呆。此事已能把天捅出一個窟窿了,即便是三個臭皮匠湊在一起,亦不能想出堪比諸葛武侯的絕妙好計。劉菃半晌方道:“此事牽連太大了,不可貿貿然告訴他們。”
呂翀聞言看向他:“可他們皆知戴兄入了死牢,如何瞞得住。再者了,咱們廢了這麼大的力氣,總不至要裝聾作啞吧。”
劉菃心知呂翀這個直腸子又是疑上他了,劉菃無奈道:“可人多嘴雜,萬一走漏了消息,又該如何是好?”
戴銑急急問道:“劉兄有何高見?”
劉菃被問得一愣,他皺眉半晌方道:“不若,咱們去尋戴禦史。戴禦史乃四朝元老,素有官聲,說不定能為我等指一條明路。”
這一意見得到了大家的贊同。他們絲毫不敢耽擱,直奔戴府而去。戴珊正在泡腳,準備就寝了。實木大盆中,渾濁的藥湯散發着濃烈的藥氣。戴珊慢慢把幹瘦如蘆柴棒的腳伸進去,發出一聲滿足的喟歎。一旁的老妻笑道:“燙一燙腳,晚間睡覺也暖和些。”
戴珊看着昏黃燭火下,妻子鬓邊的白發,心中也不由生出柔情來,他忙把腳移到角落:“你也來泡泡。”
戴夫人一愣,随即嗔道:“咱家又不是隻有一個盆了,叫下人們看見成什麼樣子……”
她的語聲在戴珊的目光中變得越來越小,她最後方道:“我纏了足,有白布時看着小巧,可解了布帶就不成樣子了。”
戴珊一愣,他握住戴夫人的手道:“你我都是即将入土的人了,何必還在乎這些。再說了,我的腳也不好看呐。”
戴夫人失笑,她的眼眶微微濕潤了,随即坐在了戴珊身旁,脫了鞋襪慢慢把腳探進去。她扭曲的腳踩在戴珊的瘦腳上面,滿是老年斑的手被戴珊同樣粗糙的大手握在掌心裡。他們四目相對,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了風華正茂時的倒影。少時夫妻老來伴,他們相伴走過人世的春秋,也會攜手到地下長眠。
許是因這溫馨的氣氛,戴夫人心中鼓起了勇氣,她忽然開口道:“老爺,你、你緻仕吧。”
戴珊暈陶陶的腦袋仿佛被誰當頭打了一棒,他一下就驚醒了:“你說什麼?”
戴夫人深吸一口氣:“妾身是說,請您緻仕吧。您和妾身的年紀都已不小了,咱們也該安享晚年了,不如回老家去,咱們還能弄一個小院子,你種幾畝地,我喂一些雞鴨鵝。孩子們回來了,咱們還能……”
戴夫人的眼睛明亮得像星星一樣,就像新婚之夜時她看到他的那一刻一般。戴珊到嘴邊的呵斥被生生咽了下去,他以沉默表明了他的态度。戴夫人太了解他了,她明白他的意思,可不願就此退縮,她道:“老爺!您……”
一語未盡,門口忽然傳來小厮的聲音:“啟禀老爺夫人,有三位給事中老爺說有大事想與老爺相商。”
戴夫人搶先一步道:“讓他們明兒再來,這都什麼時辰了!”
戴珊卻打斷道:“不,替我更衣。”
戴夫人一怔,她緊緊抓住丈夫的手:“别去了,你以為你還是年輕小夥子嗎,你都七十多歲了!”
戴珊道:“我深受皇恩,隻要還有一口氣在,就要為朝廷效命。”
他掙開了戴夫人的手,向前走去。戴夫人望着他的背影,淚水不由滾落。
戴銑等三人坐在戴家的花廳裡,竟有幾分瑟縮,一見戴珊來,亦是欲言又止。戴珊道:“何故做此小兒女态,難不成在節日深夜叫老夫出來,就是瞧你們大眼瞪小眼嗎?”
呂翀忙道:“當然不是!松厓公容禀。”
他語罷看向戴銑,戴銑一橫心,将前因後果都說了出來。呂翀則在一旁不斷補充。劉菃眼看戴珊眯成一條縫的眼睛越睜越大,最終射出刀鋒一般銳利的寒光。半晌,戴珊方道:“都回去吧,把此事爛在肚子裡,決計不要洩露半分。私入天牢是大罪。”
呂翀道:“可這事兒……”
戴珊擺了擺手:“明日,老夫就入宮面聖。”
呂翀有心再問,卻被戴銑不斷地拉袖子,他隻得閉嘴和他們一塊退了出來。出門,他方道:“你們怎麼不多問問呢?”
劉菃道:“戴禦史的為人你還不清楚嗎,他既然說了,就一定會想法子應對。咱們靜候佳音就是,若是不成,我們再想法子也不遲。”
呂翀這才被安撫下來,幾人回家去一夜未眠。而戴珊也是一宿地輾轉反側,他想到了那日入宮前,李越慘白的臉,難怪、難怪他會那樣……第二日天剛蒙蒙亮,他就起身,坐上藍呢大轎入宮去了。
朱厚照正在吃“薰蟲”,名字雖吓人,實際卻隻是面粉攤得餅而已,其中别出心裁卷上了蝦肉和木蘭芽。朱厚照吃得津津有味,問道:“這是誰進得?”
侍膳的小太監道:“回禀萬歲,是劉太監。”
朱厚照的動作一頓,頓覺嘴裡鮮香肥美的蝦肉都失去了滋味。他擺擺手,示意撤下去,小太監眼前一亮,忙趁機把谷大用進獻的雞腿銀盤菇卷餅獻上來。朱厚照正待嘗一個,就聽人回禀,戴珊求見。這下,第二個“薰蟲”也吃不下去了。他皺眉起身,擺駕武英殿。
初春的陽光還是極淺淡單薄的,透過菱花式的窗格射了進來,在地磚上投上了點點光斑。戴珊被叫起之後就賜了座,他坐在文竹方凳上,眼瞧着朱厚照坐在龍椅上,正好整以暇地望着他。
朱厚照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,戴珊此來決計不會是說什麼好話,但他沒想到,戴珊竟然會放出這麼一個驚天巨雷。戴珊道:“……老臣使人去見俞澤後,終明萬歲為難之處。老臣願為萬歲排憂解難……”
朱厚照的腦子嗡得一聲,怒火如岩漿噴湧一般直沖天靈蓋,但在觸及空氣後卻又漸漸冷卻下來,他已經不是以前那個喜形于色,随心所欲的皇子了,他終于漸漸學會了隐忍和謹慎,他甚至還露出了一絲笑意:“真不愧是戴先生,那群廢物,果然攔不住您。俞澤也同您招了?”
戴珊顫顫巍巍地起身跪下,冰冷的地磚上寒意漸漸沁入膝蓋,他心下苦笑,昨晚夫人的藥湯又白泡了。他磕頭道:“萬歲恕罪,此事是臣莽撞,但臣的确是出自對萬歲的一片忠心……”
朱厚照挑挑眉,譏诮在他的眼中一閃而過,可他的語氣卻益發和煦:“先生的為人,朕還是信得過的。此事被您知曉了,也無甚大不了。先生說為朕排憂解難,可是有良策?”
戴珊再叩首道:“劉瑾謀害世子,栽贓嫁禍,罪該萬死,臣請萬歲秉公辦理,也可給宗室一個交代。至于李越,他雖是被牽連,可因色誤事,亦動殺心,不妨找個由頭将他貶斥出京,以觀後效。”
戴珊到底對月池有幾分回護之心,找個由頭即是将她從這事中撇清幹系,雖被貶出京,可到底還可保住性命。隻可惜,這事兒從一開始就糟了。
朱厚照手上的玉戒指發出清鳴,他看向戴珊:“俞澤在你這兒招得是,是劉瑾為了害死李越,所以刺殺世子,嫁禍給李越?”
戴珊聽得語氣不對,他忙把俞澤的供詞呈了上來,問道:“難不成,俞澤在錦衣衛處的供詞不一緻?”
朱厚照看着紙上鮮紅的皿手印,嗤笑一聲:“奇了,他在朕這兒,受盡酷刑,可是什麼都沒說,怎麼先生遣人去問,一下就問出來了呢。”
戴珊怔怔地看向朱厚照,他感覺自己好像跌入了一個怪圈,無論如何也找不到出口。
六科廊中,劉菃等人亦是心急如焚,他們打聽過了,戴珊一早入宮,到如今都沒出來,而其他人則在纏問戴銑,大夥費了那麼多心力,一塊把他送進了天牢,他出來怎麼能裝聾作啞呢?其中以劉宇追問得最為起勁。他對着戴銑道:“究竟牽連到了什麼樣的人物,能把戴賢弟吓得做了縮頭烏龜。”
戴銑面有愠色,但仍咬緊牙關,劉宇心下呐喊,越發煽風點火,真個有人動了真氣。劉文端一把揪住戴銑的脖頸斥道:“你這般畏畏縮縮,真叫人不齒。”
戴銑的臉漲得通紅,他道:“不是我退縮,而是……你們别問了,我是一個字都不會說得。”
旁人見他這幅大義凜然的模樣,越法惱火。給事中葉相忿忿道:“算是我們瞎了眼,他不肯說也無所謂,大不了我們再混進去一次就是了。”
劉菃一驚,他忙道:“你們瘋了,這可是掉腦袋的事。”
劉文端斜睨了他一眼:“你以為人人都是貪生怕死之輩嗎?”
戴銑被堵得臉紅脖子粗,劉菃又忙出來打圓場,就在大家吵吵嚷嚷,熱鬧如菜市時。呂翀忽然像一陣風似得沖進來,他生性沖動,又受此沖擊,哪裡還想着保守機密,當即嚷嚷道:“大事不好,宮裡說,戴禦史要告老還鄉了!”
戴銑和劉菃仿佛挨了一悶棍,他們面面相觑,眼睛瞪得像凸眼金魚,其中卻皿絲密布。戴銑脫口而出:“怎麼會這樣,怎麼連戴禦史也?他一定是被逼得!”
劉宇打了一個激靈,他急急道:“你怎麼知道,難道戴禦史緻仕和你有關,還是有這案子有關?”
劉菃一面強笑着說沒有的事,另一邊卻對戴銑不住地使眼色。可戴銑的心中卻被悲憤和狂暴充斥,他道:“我等顧及皇上的聲名不願大肆宣揚,可皇上卻為了保全自己的顔面,一意孤行,連戴禦史這樣的四朝元老都能輕易貶斥。‘君視臣如草芥,臣視君如寇仇。’劉兄,事到如今,我們還有什麼好顧及得呢?”
劉菃為難地看向他:“可戴禦史有囑托……”
戴銑卻打斷道:“如今戴禦史自身難保,我們難道能袖手旁觀嗎?諸位,事到如今,我就實話實說了吧。”
整個六科廊裡都回蕩着他洪亮的聲音。戴銑朗聲道:“世子之薨,實是劉瑾為嫁禍李越而做的!李越與世子争搶俞氏不成,懷恨在心,而劉瑾為了害死李越,所以先下手為強,劫走俞澤,讓他殺了世子,再把罪名撇在李越頭上。萬歲為了自己的顔面和保住他兩個近臣,這才不允九卿會審!”
劉宇臉上的笑意消失殆盡,他已經僵硬成了一塊木頭,愣愣地看着衆人在一片嘩然之後,群情激憤,要去伏阙懇求皇上收回成命。他有心想要阻止,卻像掉入洪水中的羽毛一般,起不到絲毫作用,到最後,他隻能偷偷溜出隊伍,直奔劉瑾的府邸。
而在武英殿,戴珊對此還渾然不知。朱厚照明明白白地告訴他,你被當槍使了。
俞澤既恨月池将他們全家帶入這名利場,又恨劉瑾為了争權奪利,不擇手段,還恨身為皇帝的朱厚照,放縱宗室和臣下,害得他們這些平民苦不堪言,所以他都要報複。他在錦衣衛的嚴刑拷打下隻字不言,卻逮着戴銑說出了謊言,這是依着劉瑾所教,一方面是為了讓月池一命嗚呼,另一方面則是惹得宗室不滿,君臣猜忌。隻是,劉公公本來想殺了月池,沒想到卻陰差陽錯卻把自個兒也帶了進去。
而俞澤本以為帶上劉瑾,就會讓他和李越一起萬劫不複,孰不知由高層文官在朱厚照面前狀告劉瑾和李越,反而加重了朱厚照的另一重猜想。要知道,朱厚照和月池都曾想過,會不會是文官集團因對改革不滿,所以借汝王世子、李越和劉瑾的命,來打擊皇帝本人。畢竟宗室是天子的親眷,李越和劉瑾是天子的左膀右臂,一次除掉這三位,天子本人多年的布局都會為之動蕩。
一家的命案卻由于幾方勢力的裹挾變得撲朔迷離。朱厚照手中已有戴珊和俞澤兩條線,朱厚照現下打算通過戴珊查探下去,找出幕後主使。可戴珊卻不願和盤托出,他也是文官中的一份子,心知如果任由朱厚照查下去,如若真查出幕後主使是文臣,必定會興大獄,屆時不知多少無辜的清正之士會受牽連,旁人不說,就是戴銑、劉菃和呂翀三個,就必死無疑。所以,老先生把嘴閉得像蚌殼一樣,希望能在朱厚照這兒把此事到此為止,他甯願自己私下去想法子查探。
但朱厚照豈會善罷甘休,他道:“您不說,朕難道就不知道了嗎?這些天誰去了您家中,錦衣衛和東廠要查探易如反掌,朕一個個地排查下去,遲早會揪住狐狸尾巴。”
戴珊苦笑道:“萬歲,何苦要如此喊打喊殺,不若将此事交由老臣,老臣必定會給您一個交代。”
朱厚照靜靜地看着他,他深棕色的瞳孔在澄澈如水的日光下如琉璃一般,他溫言道:“先生已然年老,朕早就有意讓您衣錦還鄉,安度晚年,又怎能再勞動您。”
戴珊的心沉沉地墜了下去,他是個堅強的人,可到底也是皿肉之軀,如何經得起一次又一次地重創?他想起了老妻的話,終于心灰意冷了。
他的頭在地磚上發出一聲悶響,眼中孝宗皇帝蒼白瘦弱的面孔一閃而過,渾濁的淚水順着他的眼角劃過,他輕輕吸了吸鼻子,開口道:“那就請萬歲,允老臣緻仕吧。”
戴珊在說實話和緻仕之間,選擇了緻仕。這的确有點超乎朱厚照的預料,但他沒想到,讓他吃驚的事還多着呢。就在朱厚照拟旨之後,殿外忽然傳來了隆隆的鼓聲。六科廊的給事中們敲響了登聞鼓。
李家中,時春急匆匆地奔回家,沖進了月池的書房,在月池疑惑的目光中,喘着粗氣道:“出大事了,有文官敲了登聞鼓,棋盤街那兒的人都吓壞了,好像還是為了那樁案子!”
月池霍然起身,她放在桌上的茶盞因這動蕩摔得粉碎,濺了大福一身的茶水。狗子不高興地直叫,可月池已經顧不上它了,她的面容像玉像一般,輕聲道:“叫他們備馬,我要立刻進宮。”